Sabry原则:兼谈了解机理的重要性
作者:路人丙
今天读到一篇文章提到Sabry原则,源自基因泰克的一位研发高管James Sabry。这个规则说除非有机理相关的生物标记否则一个项目不应开始临床开发。这个规则没有Lipinski的5规则有名,可能只反映基因泰克的研发理念。但基因泰克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研发公司之一,所以或许这个规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找到机理相关的生物标记首先得知道机理,难道机理未知的药物都不应该到临床开发了?基因泰克作为一个以开发抗体药物为核心的企业,当然多数项目都是机理已知的(据我所知尚未有机理未知的抗体药物),而他们抗体药物的巨大成功肯定也会影响他们小分子药物的研发策略。关键是这个理念对整个药物研发意义有多大,机理未知是多大的风险。
机理是否重要业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机体太复杂,无法有效根据机理设计药物。机理未知也不容易被其它企业跟踪me-too,所以竞争上占优势。在现在研发经费向机理为中心模式高度倾斜的情况下机理未知的新药依然占很大比例也说明机理未必是药物成功的先决条件。当然更多的人认为机理和其生物标记相当于你半夜下楼时的楼梯把手,扶着它楼梯虽复杂你摔跤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所以了解机理可以降低整个研发过程的风险。新药研发比黑灯下楼复杂无数倍,失败比摔一跤痛苦无数倍,所以如果知道机理能降低失败率当然花精力找到这个机理是值得的,但实际情况是否是这样呢?除了罗氏Swanney的那篇Nature Review文章,好像没有真正的数据分析机理在药物研发中的作用。现在没有系统的数据证明机理未知一定失败率高,或者机理已知就增加成功可能。那为什么多数人会坚信机理如此重要呢?
第一我认为很多重要项目的失败可以归罪于机理的未知或错误使用。2008年著名的阿尔茨海默药物dimebon,辉瑞除了知道它在俄国的一个实验疗效不错之外几乎对它一无所知,结果三期临床失败你根本不知到底哪出的问题。如果知道机理,至少可以挑选那些从机理上看更有可能应答的人群,或根据生物标记数据更科学地选择剂量。2006年一个CD28抗体由于错误计算受体占有率(人和猴子的受体表达水平不同)结果剂量过高,导致6个一期临床志愿者全部进了ICU,公司因此破产。这只是受体表达水平差异的计算失误,如果根本不知是什么机理你更没有机会估计正确的剂量。最近DMD药物Drisaspersen的失败也是因为二期临床生物标记没有显著改善就进入三期临床而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已有的不需要机理信息的筛选优化模型已经过了黄金时期,能找到的药基本找的差不多了,再向未知扩展必须有一定的依据。机理未知药物主要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现在多数企业已经离开这个领域,所以以后产出自然会下降。虽然没有证据了解机理可以降低总风险,但有些具体风险的解除必须依赖机理,比如寻找合适的治疗人群,剂量。拿现在白热化竞争的PD-1来说,哪个肿瘤、已经用过何种治疗药物的肿瘤PD-1过度表达、过度表达到何种程度是你选择关键3期临床的重要根据。如果选错了,很容易浪费几个月的宝贵时间,而这几个月将决定你第一还是第二上市。在现在的支付环境下这几个月可能会造成几十亿美元的销售区别。人和动物同一蛋白结构和表达水平可以相差很大,甚至人有的动物根本没有或动物有的人没有。如果动物和人的蛋白有区别,在研究阶段就得寻找在这两种蛋白都有活性的化合物。否则你可能找个特效老鼠抗癌药。
在对药物附加价值的要求日益增加的环境下,更早地对药物机理的深入理解是寻找有区分药物的保证。最近辉瑞的研发人员提出新药项目的三个支柱,即药物需要在靶标组织有足够时间浓度达到治疗浓度,显示的确和靶标蛋白结合,并且药理结果和药物机理一致。这和Sabry规则不谋而合。
当然知道机理并不能保证你成功,而且当机理为中心成为主流后这个模式失败的项目自然会增加,因为项目总数增加了。但是90%的机理已知药物最后失败并不能说明机理未知成功率会更高。阿司匹林的成功同样不能说明机理是否清楚无所谓,现在研发成本和审批严格程度都远比阿司匹林时代高,即使微小的成功率区分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一个失败就可以令小公司破产,大公司元气大伤。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现在的重要药物很少是机理未知的。Sabry规则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研发风险,并不是说机理未知的药物一定不能成功,只是有些人认为这个风险太大,不值得冒。这就跟网恋一样。有没有成功的,肯定有,但多数人认为这是风险很大的一个交友方式。
美中药源原创文章,转载注明出处并添加超链接,商业用途需经书面授权。★更多深度解析访问《美中药源》~
★ 请关注《美中药源》微信公众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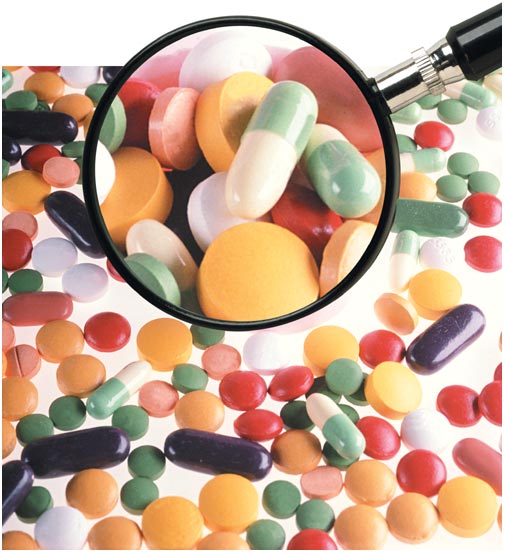

















 微信号:美中药源
微信号:美中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