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苗头化合物的结构特征和蛋白结合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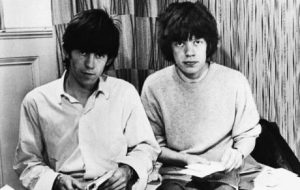
【新闻事件】:今天《药物化学杂志》发表一篇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的一项工作。作者分析了20个蛋白家族中126个蛋白与462个片段苗头化合物的复合物晶体结构,涉及168个结合腔(有的蛋白有不止一个结合腔)和79个蛋白域。宏观性质看这些分子片段的95%符合RO3规则(MW<300, clogP<3,氢键供体<3),90%是非手性化合物,sp3杂化碳原子也不多(Fsp3<0.5),但71%化合物至少有20-30%的原子是可以形成氢键的杂原子。73%的片段配体在晶体结构中至少有80%表面被蛋白结合腔覆盖, 77%的化合物至少80%的极性表面被蛋白覆盖。92%的片段至少与靶点蛋白形成一个氢键,其中88%是埋在结合腔内的高质量氢键。分辨率较高(<1.5埃)的晶体结构可以分析水的作用,这些结构(116个)中46%至少有一个水分子与蛋白形成两个氢键、与配体形成一个氢键。以较小代价通过片段筛选找到这些优质结合方式再优化可能是个效率较高的药物设计策略。
【药源解析】:小分子药物发现首先要有一个性质比较接近药物的先导物。历史上先导物主要来自天然产物和临床的意外发现。后来有人发现有些化学结构与多类蛋白结合,这些所谓优势结构的衍生物可能成为多个靶点提供先导物。随着组合化学和高通量测试的兴起有了高通量筛选(HTS)和最近的DNA编码库筛选(DEL),可以为多数靶点找到活性足够的苗头化合物。但筛选都是以活性为首要评价指标,而现在化合物库中很多化合物其它性质不佳,这令药代、毒性、选择性等下游性质的优化变得困难。
HTS如同买彩票,要买到6个数全对的几率很小。但如果你能以少量投入先找出一两个正确数字再用某些算法推算其它数字则效率增加很多,这是基于片段药物设计(FBDD)的初衷。FBDD通常只要筛选几千化合物(HTS需要几十上百万,DEL筛选几十亿稀松平常)即可找到配体,但这些配体通常活性较低、在0.1-1 mM范围。找到候选药物并不容易。回到上面彩票的算法,在FBDD中这个算法就是晶体结构。有了晶体结构(或溶液结构,但不常用)的指导化合物修饰可以有的放矢,比随机筛选理论上效率大增。多年前Michael Hann用了一个简单数学模型证明片段筛选的命中率高于HTS,但代价是离终点更远。
除了命中率,这个工作的两个主要发现、即片段分子大部分表面被蛋白腔覆盖和极性相互作用(氢键和结构水介导氢键)驱动结合也是药物分子的理想性质。极性相互作用因为对方向和距离有严格要求所以分子越大越不容易同时有多个配体-靶点极性相互作用。这个工作对比了另一个数据库中445个HTS化合物与靶点的晶体结构,发现这些平均分子量比片段大一倍的化合物只比片段多一个与靶点作用的氢键。这些极性相互作用也不容易在结构修饰中加入,你随便翻开一篇J. Med. Chem文章会发现化合物优化过程中90%的活性增加来自疏水基团的引入。所以迅速找到一个关键极性相互作用是个优势,如同组建乐队已经找到主唱。这个氢键供体如果在一个较大化合物中可能因为位阻或其它平衡因素无法被发现。片段更可能深入结合腔也比较容易理解,但这个工作发现片段的极性表面也比较大化合物更容易被结合腔包围,虽然差别不大但也是个优势。
片段虽然有不少优势但也有实际困难。首先检测这样弱的活性需要另一套评价系统、多数为生物物理技术,这是附加成本。另外对于复杂蛋白因为技术限制通常只能用其中一段测试,与这段蛋白结合不一定能在功能上抑制该蛋白,因为有些结合腔对功能无影响、而有些蛋白域的存在会调控活性腔构象。另外从片段开始即使有晶体结构指导优化过程还是要长于HTS,这也是不利因素。FBDD已经有了几个上市药物,但与DEL类似只是对某些特定靶点会起到重要作用,彻底取代HTS目前不太可能。
原文见: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jmedchem.8b01855
美中药源原创文章,转载注明出处并添加超链接,商业用途需经书面授权。★更多深度解析访问《美中药源》~
★ 请关注《美中药源》微信公众号 ★



















 微信号:美中药源
微信号:美中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