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药一世界:新药管线的球星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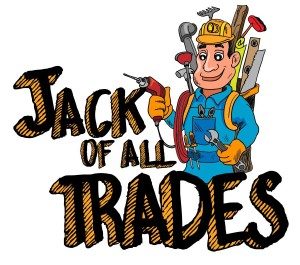
【新闻事件】:过去10年大药厂进入三期的新产品稳中有降,无论自己研发、买入、还是收购其它公司的三期资产都同步下降。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数目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厂家把赌注压在少数明星产品上、形成了所谓pipeline in a drug现象。事实上每个三期资产的平均适应症确实在增加,从2011年的1.2个增加到1.7个。虽然绝对数只有0.5个,但这是42%的相对增长、还是说明一定问题的。
【药源解析】:过去10年的一个黑天鹅事件是PD-1药物的横空出世,这些药物令很多晚期肿瘤成为可以治愈的疾病。因为这样长期深度应答药物极少遇到、竞争十分激烈,加上临床前评价技术脱节、预测哪些适应症可行比较困难,所以很多厂家觉得三期临床作为一个筛选机制是一个值得冒的风险。仅2015年一年,K药就开始针对9种肿瘤的14个三期临床。当然PD-1也不是极端个例,在此之前的TNF抗体也是著名的十项全能药物,修美乐至少有10个不同标签、在很长时间内支持艾博维的生存与发展。更早的神药阿司匹林、二甲双胍也是越活越年轻,要不是因为专利早就过期影响了制药业的热情还不知道要增加多少适应症。
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某些重要通路在多种环境下影响生命功能、改变疾病进程,而关键操盘手通常是一些功能广泛的野生型蛋白。制药业开始于跟踪表型变化如动物模型或临床偶然发现,70年代以James Black为代表的现代药物猎杀开始了所谓靶点为中心新药发现模式。刚开始就是靶向一些野生蛋白,如H2受体。但是随着标准疗法的改进和新药技术的飞速发展,野生靶点选择性差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在肿瘤领域。变异蛋白经常与野生蛋白存在一些结构差异,所以可能设计一些正常组织毒性较小的所谓靶向药物。格力维第一个显示了这个策略威力,几代EGFR抑制剂也大大改善了部分肺癌的治疗。NTRK、RET、ROS等变异靶点因为正常组织没有所以成为生物制药追逐的目标。因为高选择性和高活性有些药物甚至成为泛靶点药物,可以用于任何有这个变异的肿瘤。
这个策略当然有其优势的一面,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群的局限性。毕竟肿瘤来自五湖四海、并不靠一两个变异混江湖,比如只有1%肿瘤患者有NTRK变异,基因变异遗传病也通常人群很小。反过来PD-1药物并不需要你的PD-1有什么异常,所以适用人群大很多。当然并非所有患者都对PD-1药物敏感,但是这是因为肿瘤普遍狡猾,同样有Kras G12C变异但CRC比肺癌对Kras抑制剂敏感程度差很多。PD-1、TNF的例子说明靶向野生蛋白药物不一定就治疗窗口低,而且一旦找到一个这样优质靶点向其它适应症扩展的空间比依赖变异靶点更大。在一定程度上靶向野生蛋白把风险前置了,真正收获的季节是后面适应症的扩展。针对变异蛋白虽然早期容易找到高选择性药物,但后面适应症扩展难度较大、即使已经上市的泛组织药物其实在不少肿瘤的疗效是存疑的。当然这两个策略各有千秋,哪个用好了都可能产生重磅药物。只是在精准疗法的大潮下制药工业可能高估了变异靶点的优势,野生蛋白才是出产平台药物的地方。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美中药源原创文章,转载注明出处并添加超链接,商业用途需经书面授权。★更多深度解析访问《美中药源》~
★ 请关注《美中药源》微信公众号 ★



















 微信号:美中药源
微信号:美中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