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成药空间:最近10年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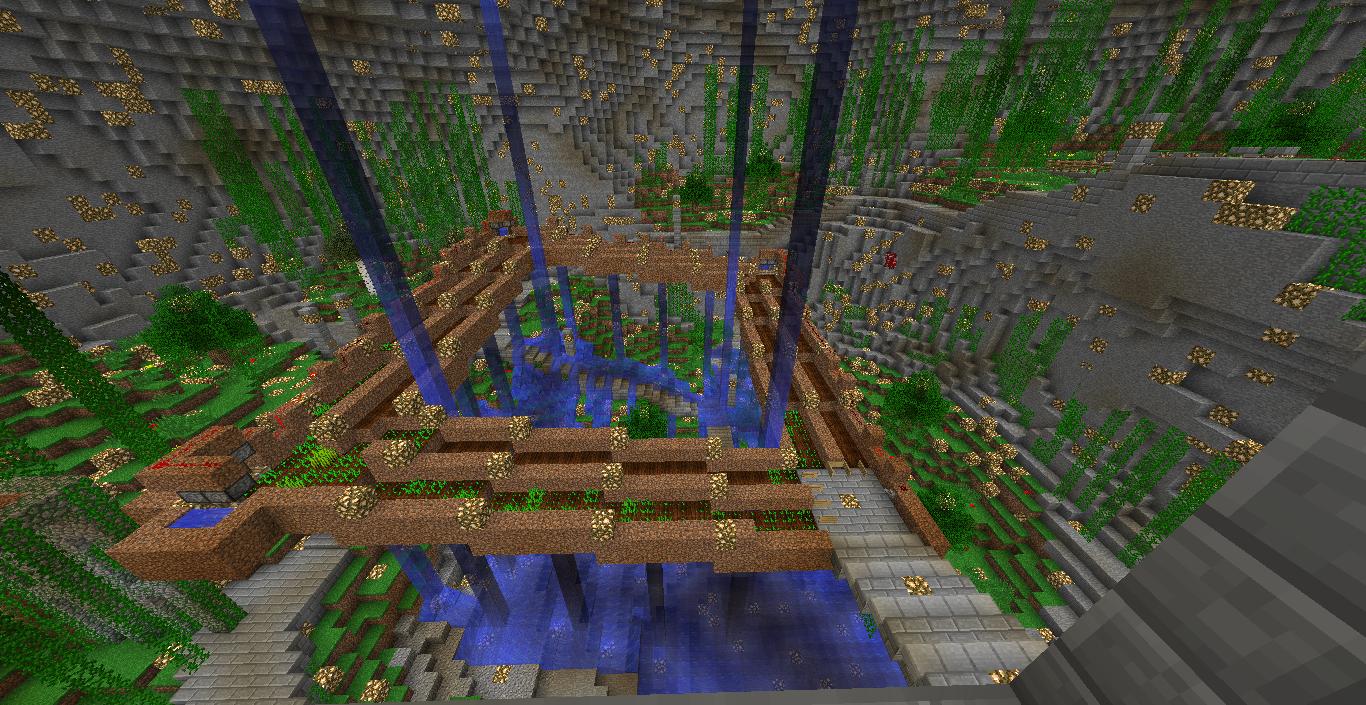
靶点的新颖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药的价值,所以发现、确证新靶点是新药研发的一个核心任务。2016年进入临床研究的新靶点有300个左右,而进入二/三期注册临床研究的新靶点不超过50个。2006到2015的10年间,制药工业共找到111个新成药靶点,平均每年11个,高于历史平均值。其中大多数仍然是传统的细胞表面受体如GPCR(15个)、离子通道(8个)、表面抗原(3个)和细胞内部的各种酶(52个)、尤其是蛋白激酶(17个)和蛋白水解酶(3个)。从上市药物靶点组成看,虽然最近10年制药工业拓展成药空间进展缓慢,但仍有少数重要突破,而更多颠覆性技术已经进入上市前的临床研究。
细胞表面受体因身处细胞表面所以药物分子不需要穿透细胞膜即可起效,令很多极性大、分子量大、外排泵底物等无法进入细胞膜的化合物也可能成药,所以发现针对这类靶点药物的几率大于细胞内靶点。细胞表面受体负责检测环境的微妙变化,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和多种类型配体结合,也增加药物发现成功率。对于只和分子量较大配体结合的表面受体,多肽药物的开发近年来也有长足进步。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抗体技术近年也发现多个针对表面抗原的高活性、高选择性抗体药物。2016年抗体药物首次超过小分子药物成为新药的头号主力。
细胞内成药靶点以各种酶为主。一是因为酶的结合腔通常能和小分子药物高效结合,另外很多酶除活性口袋外还有天然的别构调控位点可以与药物分子结合。绝大多数药物是酶抑制剂,酶激活剂的发现非常困难。酶抑制剂的体内、体外评价相对简单,也是大家热衷这类靶点的原因之一。蛋白激酶是最大的一类酶,对生命过程十分重要,但找到高选择性的激酶抑制剂仍然是个主要技术障碍。目前除个别例外(如Xeljanz),只有选择有限的肿瘤患者可以容忍激酶抑制剂的副作用。由于激酶生物学、蛋白结晶、有机合成技术的同步进展,过去15年是蛋白激酶抑制剂开发的黄金时期,现在已有30几个新药上市。
但是对现有疾病有重要影响的蛋白不仅局限于表面受体和酶,即使受体和酶也有很多因为高活性、高选择性配体太难找到而无法成药。制药工业急需扩展成药空间,但这需要多门学科的协同努力,并非一日之功。虽然进展缓慢,但过去10年还是有一些令人振奋的突破。例如蛋白蛋白相互作用这类传统的高难靶点今年终于被制药业攻克,2016年FDA批准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药物、BCL抑制剂Venatoclax。这得归功于过去10年基于片段分子设计和蛋白结晶技术的成熟,这大大改善了这类靶点的成药性。
另一个靶向难成药靶点的策略是在RNA水平调控蛋白活性。过去10年FDA批准了三个反译RNA药物(Mipomersen、eteplirsen、nusinersen),其中nusinersen的两个三期临床试验因疗效显著被提前终止。这个药物治疗儿童第一杀手脊髓性肌萎缩症,所以可能成为第一个主流RNA药物。siRNA药物如针对PSCK9的PCSK9si在二期临床试验中显示非常显著疗效,mRNA、miRNA药物也开始进入临床阶段的开发。
基因疗法和mRNA药物不仅可以作为蛋白抑制剂也可以激活蛋白活性,这是和传统药物的一个重要区别。2012年欧盟批准了西方市场的第一个基因疗法Glybera,现在还有多个针对各种罕见遗传疾病的基因疗法正在中晚期临床开发中。细胞疗法如CAR-T过去5年进展神速,不出意外的话诺华和Kite的CAR-T疗法都将在主要市场上市。治疗性肿瘤疫苗虽然举步维艰,但是因为其它免疫疗法的快速进步也可能成为未来肿瘤组合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药成药空间的扩展十分艰难,一两门学科的进步难以推动整个领域。过去10年虽然传统的小分子、抗体药物的成药空间几乎没有扩大,但RNA、DNA、细胞疗法、治疗疫苗等新技术开始成为触手可及的疆土。这些技术无疑还处在婴儿期,但是都已经通过了最关键的概念验证阶段。下一个10年可能会成为收获期,很多疾病的治疗有望发生质的改善。
美中药源原创文章,转载注明出处并添加超链接,商业用途需经书面授权。★更多深度解析访问《美中药源》~
★ 请关注《美中药源》微信公众号 ★



















 微信号:美中药源
微信号:美中药源